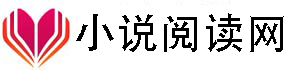170-180(38/44)
占用假期时间是不可能的,再着急的事情也得等到年後。主要是过年前後他的肱股之臣们都在忙家里事凑不到一起,他本来的打算就是年後召集政事堂和条例司的官员坐下来好好说话。
过年放松几天,他也好真正静下心来考虑接下来要怎麽办。
这一年来只顾得闷头和朝臣吵架,回头看看的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幸好政事堂的几位相公没有全部被他气跑。
青苗法往哪个方向改他还没想好,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还钱时的那两分利必须得取消。
官府可以不借钱给百姓,但是绝不能在需要粮食救命的时候找百姓收利息。
至于家中贫困到什麽程度才能找官府借粮,还得商量过之後才能决定。
这份钱不是赈济救灾的钱,赈灾的银两花出去回不来,青苗钱花出去还得要回来,要是二者混为一谈,朝廷又何必费劲去推行青苗法?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仓促推行下去问题太多,新政果然还是得慢慢来。
赵大郎转身想走,他已经知道在他爹上头的时候说服他改变主意有多费劲,短时间内他不想和他爹讨论新政相关的事情。
他还是个孩子,他懂什麽?
切~
然而他想说的时候他爹不让他说,他想走的时候他爹又不让他走。
官家成年许久终于迎来了叛逆期,这个叛逆期还全使在亲儿子身上了。
太子殿下:……
说真的,他感觉他这个儿子比当爹还操心。
行吧,让他看看他爹又有什麽奇思妙想。
事实证明,让王相公和其他几位相公坐下来好好说话正这个法子根本行不通,不管之前说的多好,几个人凑到一起都会演变成吵架。
冷静是冷静不下来的,只要人凑到一起,在朝堂还是在书房没有区别,总之吵就完事儿了。
火气上头的人是没有理智的,冷静时分析利弊的能力消失的干干净净,满脑子只有不行不许不可以。
谁都说服不了谁,谁都不觉得自己有错。
把人凑到一起心平气和商量对策是行不通的,最管用的法子就是他两边来回跑当个善解人意的传话人。
只能他来当,换个人都不行。
当过传话人才知道传话人有多难当,尤其是一方说不清楚另一个又不乐意听解释的时候,真没人在其中调停朝堂都能让他们吵翻天。
条例司推行的均输法和汉时理财名臣桑弘羊推行的均输法名字一样,但是内容却有很大的不同。
王相公他们知道他们的均输法和史上那些均输法名字一样内容不一样没用,读过书的都知道桑弘羊推行均输法虽然帮助汉武帝渡过财政危机但也招来了一身的骂名,很多大臣都觉得两个法是同一回事儿,用那麽多年前的疏漏百出的旧法当新法也不嫌丢人。
于是乎,吵吵吵吵吵吵。
用他们家小郎的话来说就是一方没长嘴一方没长耳朵,本来两页纸就能讲清楚的事情最後拖拉到两万页都讲不完。
汉时的均输法是买贱卖贵,先用地方赋税买当地最便宜的货物然後转运到别处高价卖出,这的确是在和商贾抢生意,桑弘羊挨骂不亏。
但是他们王相公想推行的均输法和旧有的均输法除了名字相同其他差别大了去了,桑弘羊当时主要是为了让朝廷渡过财政危机,王相公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大商人囤积居奇以及改善东南六路百姓的生活,前者是赚差价,後者是平物价,但凡两边能成功对接,朝堂上都不至于吵成之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