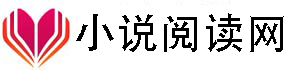180-190(6/40)
若是再派皇城司的探子去地方,让条例司原本负责这些事情的官员如何自处?这算什麽?不信任他们?
王安石沉默了一会儿,表情不太好看,“条例司八个检详文字官走了四个,你觉得相度利害官能好哪儿去?”
程颢、刘彜那几个家夥回京後明确表示不支持继续推行新法,在苏子由开了个主动请辞的头之後也都跟着请命调去其他衙门,一个个的都有主见,他管得住哪个?
苏洵:……
那也不是他们家子由的错。
老苏在心里嘀咕,嘴上也没闲着,“景哥儿信上说的没错,青苗法的目的是救济百姓,但是对那些根本拿不出利钱的百姓来说几成利息都没有区别,不管利息多少他们都负担不起,找官府借钱官府不一定愿意借,最後依旧只能借那些富户的钱。”
不是说朝廷就该无偿借钱给百姓,而是对那一部分百姓来说,朝廷的确不该收息。
王安石无声叹气,“条例司在推行青苗法上制定了那麽多细则尚且一团糟,你觉得地方官会老老实实的只收富户的利?”
最大的可能是利息依旧是贫民出,不收利的那部分钱被地方官自己把持。
苏洵想说大宋官员的整体水平还没差劲到那种程度,可是回头看看之前半年的情况,还真他娘的能差劲到那种地步。
算了算了,去开封府问问江湖人的情况,地方官的人品靠不住,只能在监察上下功夫了。
俩爹风风火火出门,留下仨孩子茫然不知所措。
他们接下来要干什麽?继续吃烤番薯?
三个人看看整洁的书房,果断换个地方聊天。
苏轼本来被贬为杭州通判,没想到任命书刚下来就又被官家收了回去,也不知究竟是福是祸。
所幸大苏心态好,在哪儿当官都是当。
苏辙年後就要离开京城前往洛阳,条例司的政务交接完毕後没什麽要忙,已经在家闲了好几天。
兄弟俩在家不想提糟心事,想着王小雱明年秋闱要下场于是开始问功课。
他们俩都是过来人,还是近两届的过来人,王相公要改科举也改不到下一届,所以王小雱有什麽事情不懂问他们比问王相公更合适。
王雱深吸一口气,要不还是继续说登州的情况吧,朝堂也可以,只要不提功课说什麽都行。
倒不是说他的功课不好,而是最近帮他爹编《毛诗义》编的他看见书就头疼。
苏轼眨眨眼,“《毛诗义》?相公真的要改官学用书?”
王雱点头,“书已经编的差不多了,即便明年不改,後年也是要改的。”
他爹亲自编写《周官新义》,《毛诗义》《尚书义》是他和吕惠卿来编,读书重在经世致用,空谈诗文无甚用处,文言论策才是取士之重。
大苏小苏对这事儿倒是没有太大意见,主要是有意见也没用,王相公新教材都快编好了,除了官家没人能叫停。
就是这麽一来,王小雱明年秋闱下场压力可就大了。
这倒霉孩子,唉,王相公也真是,好歹等儿子考中进士再让他插手这事儿。
条例司的属官又不是全都不支持新政,虽然反对的声音大,但是总体来看支持的也不少,吕惠卿曾布等人的学识都很出衆,何必这时候就让王小雱掺和进来?
王雱跟着叹气,好在他觉得他应该不会给他爹丢脸,提前掺和就提前吧。
就像他们家景哥,没开始当官就先帮着开封府破案。
差不多差不多,明年秋天再紧张也来得及。